镜子天生就是个乐观的“两面派”。时常听到有人提问:为什么铜镜图片都是镜子的背面,而没有镜子正面?铜镜的正面到底长啥样?看来大家对古代镜子充满了好奇心,希望看到铜镜正面。这促使我翻检群书,采撷具有正、背两面的铜镜图片,回馈读者。
汉风遗韵
1953年12月17日,在洛阳烧沟2号西汉中期墓发掘出一面星云镜。这是一座平顶空心砖双棺室墓,两室各葬一棺,棺木已朽,仅存少量棺板灰,右棺残存漆皮较厚,推测应该是棺内为朱色,棺外为黑色。左室棺木未加漆。两棺内人骨架均化为粉末,从遗迹来看,应是头北足南。在骨架粉末之下,右棺清理出铁剑、铁刀、铜带钩各一件;左棺出土一面星云镜,一件小铁刀。从棺内随葬品来看,似右棺为男,左棺为女,即这面星云镜见于女棺之中,出于身体左侧肋部。墓内同出其他器物较多,有陶器、铜器及五铢钱等。
洛阳烧沟2号西汉墓左棺室出土的星云镜,我只是在读《洛阳烧沟汉墓》发掘报告时,看到过黑白照片与拓本,从来没敢奢望有一天能拿着实物仔细观摩。2012年12月,为编纂《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一书收集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我从北京回到了故乡洛阳。12月27日下午,在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库房里,看到了这面烧沟汉墓出土将近60年的星云镜。手捧着两千多年前的汉镜,似乎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略感遗憾的是,这面星云镜正面已是红锈遍体,偶见绿锈,仅有局部略显镜子原有的光泽,镜面左上部有一条纤细、不易察觉的纵向裂缝。镜面下部有今人书写的白色文物编号,“LSM2:1”表示洛阳烧沟2号墓出土的第一件器物。此外,我还注意到1955年9月洛阳矿山机械厂58号东汉墓出土的四乳龙虎镜,背面纹饰为两龙两虎相间配置,正面大部分已被红斑绿锈所覆盖。
据何堂坤先生研究,新铸铜镜经镀锡并打光之后,正面应是光亮崭新的,背面为纹饰,不作映照,色泽灰白。但是,镜子在使用、保管过程中,与人体、空气接触频繁,镜面上的锡容易被氧化,镀层会受到腐蚀使得镜面变黑。东汉徐幹诗作《室思》其三“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说的就是镜面氧化腐蚀的现象。
笔者以为,烧沟2号汉墓出土的星云镜,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重新被发现。随着保存环境的数次变化,镜面包裹重锈在所难免。好在镜背锈蚀较少,星云纹清晰可见,彰显着汉镜独有的韵味与质朴。围绕着圆形镜钮与钮座,在其外饰以诸多大小不一的乳丁纹,其间穿插、连接弧形短线,展示着汉代人的灵动与巧思。因镜背纹饰形状犹如天文星象,所以被称为“星云镜”。《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经典之作,2号墓出土星云镜亦因名列其中而成为永恒。汉代日光镜上的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说的是明镜,虽然烧沟星云镜正面覆锈,却是汉风犹存。
洛阳烧沟汉墓、洛阳矿山机械厂东汉墓出土铜镜均为考古发掘品,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收藏的上万面铜镜一般都是传世品,其中有4面与众不同的汉代透光镜,值得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面西汉昭明镜。
上博馆藏的这面略带神秘色彩的透光镜,从外表看起来就是一面极其普通的西汉昭明镜。正面呈灰白色,无锈,似乎照不出人的面容。背面钮座及部分宽平镜缘处附着红斑、绿锈,铭文带及镜缘局部无锈,散发着金属的自然光泽。圆钮座,内区有一同心圆及八曲连弧纹,外饰一周铭文“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兮不世(泄)”。直径12.1厘米(图1-1、1-2)。

图1-1 上海博物馆藏西汉昭明透光镜背面(《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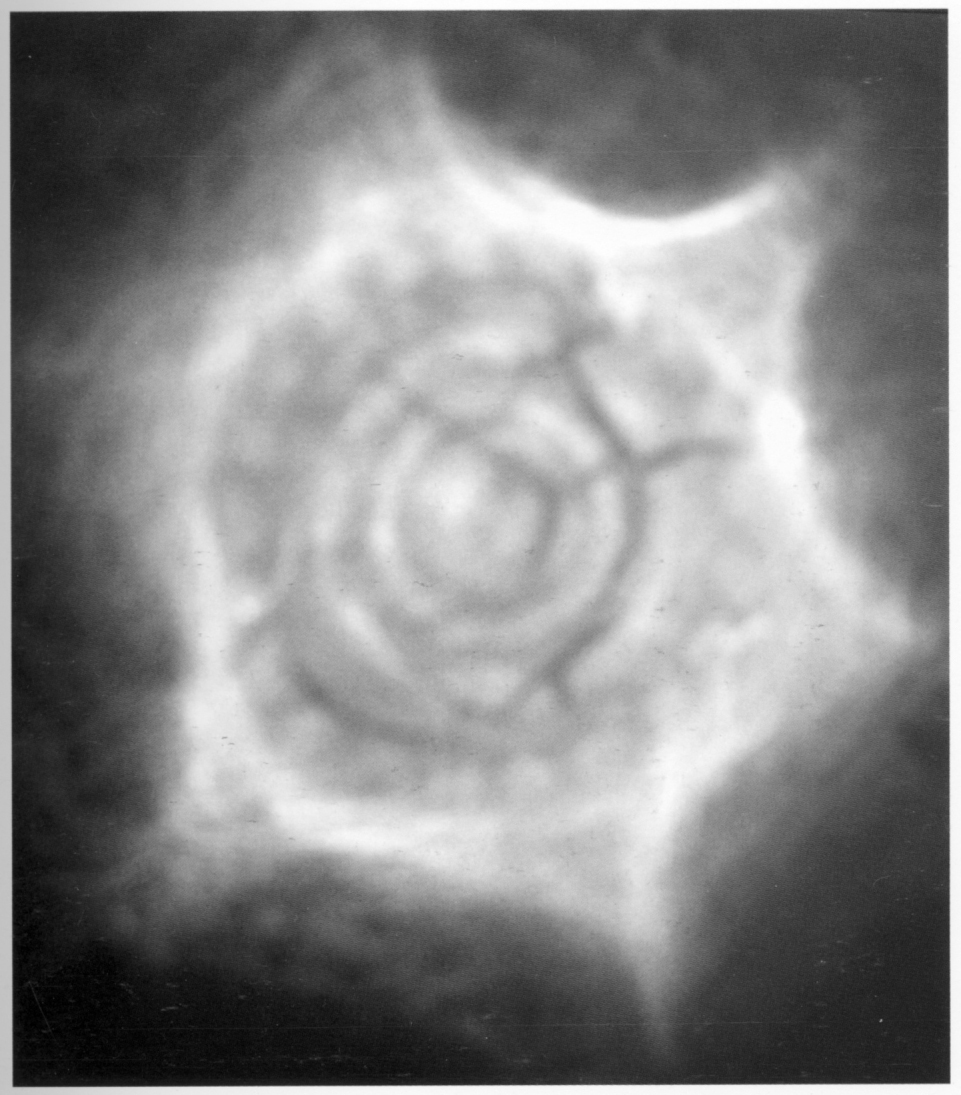
图1-2 上博藏西汉昭明透光镜反射像(《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
据上博编纂的铜镜图录介绍,这面镜子不仅正面微凸,平滑光亮,仍可鉴人,更为神奇之处在于,若有阳光或直束光线照耀背面,镜面就能反射出与镜背纹饰、铭文相对应的模糊亮影。另有一种透光形式,是当光亮的镜面承受日光或灯光(聚光)时,墙上就能反映出与镜背相对应的图像,所以被称为“透光镜”。这种镜子能透光的原因,经过模拟试验发现,主要是与镜背纹饰的结构有关。有人认为,北周诗人庾信《镜赋》中所言“临水则池中月出,照日则壁上菱生”,描写的就是透光镜的透光现象。
上博除了昭明透光镜之外,已公布资料的还有一面日光透光镜。这面日光镜外表看起来平淡无奇,与一般的西汉日光镜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直径7.4厘米。但是,如果有光照射在镜面上,也能将纹饰映照于墙上,或是由镜背打光,于镜面上反映出与镜背纹相对应的亮影图像。
上博还流传着一段与透光镜有关的故事。据《青铜大家:马承源传》一书记载,196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上博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工作人员将库房中最好的文物取出来让客人欣赏,其中就有一面西汉透光镜。客人对此镜很感兴趣,特地把镜子拿到窗口上反复观看,感叹这种透光现象的神奇。还手捧着镜子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对透光镜的原理做了种种推测。临走之前,还叮嘱上博专家要好好地做工作,把透光镜的原理搞清楚。后来,上博组织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攻关,经过不断实验,终于弄清了汉镜透光的原理。在来上博参观、观赏透光镜的这位客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上海交大制作了一面精致的镜子,反射在光影中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
上博神奇的透光镜让我们浮想联翩,能够见到这种镜子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当然,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有那么一天,偶然的机会让你有幸用古代的镜子照一下自己的尊容,体验一下当古人的感觉。1977年,西安灞桥区出土一面东汉尚方博局镜,通体乌黑发亮,俗称“黑漆古”,品相上乘。曾有一位幸运者不仅用此镜照容理妆,而且还留下了难得一见的图像资料。我也曾在洛阳有过类似的体验,镜中的我看起来朦朦胧胧的,恍然若梦。
晋镜残月
由于西晋王朝存在的时间较短,仅有52年,流传至今的西晋铜镜可谓凤毛麟角。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洛阳所见西晋铜镜数量较多,主要得益于洛阳是西晋的国都,发掘出来的西晋墓葬众多,有不少墓都随葬有铜镜,尤其以“位至三公”铭文镜最多,最具特色,推测这类镜子应是洛阳本地生产铸造的。
想找到一面西晋“位至三公” 夔凤镜的正面图片,还真不容易。2006年,洛阳吉利区2491号西晋墓出土一面残镜,有一种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残缺之美,正如当下许多年轻人放着完整的牛仔裤不买,非要穿两个腿上有若干个破洞的裤子,追求的似乎也是残缺美。若仔细观察镜面,会发现出土时镜子局部已破损,目前看到的图像是铜镜修复之后的面貌。镜面上覆盖着绿锈,上部的小洞昭示着它不太平凡的经历。
与这面镜子同出一墓的,还有四系罐、空柱盘、槅、耳杯、仓楼、灶、井等陶器,另有陶鸡、陶鸭等。更为离奇有趣的是,在距此墓不远的另外一座西晋墓内,还发现了一枚距今约1700多年前的鸡蛋壳,名副其实的土鸡蛋壳。看来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一切发现皆有可能。
此外,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经征集到一面西晋龙虎镜,龙虎隔钮对峙,均为侧面形象,龙角后伸,张牙舞爪,半个身躯如被镜钮所压(图2-1、2-2)。其镜面局部光亮如新,历经一千余年,尚能保持如此状态,实属难得。

图2-1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西晋龙虎镜背面(霍宏伟摄影)

图2-2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西晋龙虎镜正面(霍宏伟摄影)
无论是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星云镜,还是上博馆藏的透光镜、西安所见尚方博局镜,骨子里透出的皆为汉家气魄与豪情。而西晋的“位至三公”夔凤镜则略显寂寥,单薄的镜体与无光的镜面,虽然映照不出那时的精致,浅浅的色调却散发着一种淡淡的优雅与古朴气息。
大唐恢弘
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达到鼎盛的王朝,唐镜是中国铜镜史上的巅峰之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发现的唐镜数量众多,形制多样,但同时发表铜镜正、背两面图像的资料寥寥无几。
2007年,在洛阳吉利区坡底村发掘2502号唐墓,于墓室东北隅、人骨架足端出土两面铜镜。一面是直径10.7厘米的四瑞兽葡萄镜,另一面是最大径仅有3厘米的四叶镜,同出有陶器、银钗及铜钱等。由于在地下埋藏了一千多年,两面镜子的正面均为锈迹斑斑,露出部分原有灰色镜面。让人略感欣慰的是,镜背纹饰上绿锈相对较少,无论是生机盎然的花叶、葡萄,还是攀爬于枝蔓间充满活力的瑞兽、禽鸟,都洋溢着盛世的气氛,扑面而来的是“花舞大唐春”的气息。
1980年,浙江绍兴县坡塘乡曙光大队出土一面唐代飞鹤飞仙镜。此镜的独特之处,在于正、背两面,通体翠绿,绿得诱人,仿佛一池深潭,被称为“绿锈古”。
上述四瑞兽葡萄镜、四叶镜及飞鹤飞仙镜,皆属于一般工艺镜,镜面保存状况不甚理想,或为重锈覆盖,或昏暗无光,而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面镶嵌螺钿高士宴乐镜则为特种工艺镜,特殊的制作工艺使之镜面大部分保存完好,光亮如初(图3-1、3-2)。1955年,此镜于洛阳涧西矿山机械厂唐兴元元年(784年)陈曦夫妻合葬墓出土,现在国博“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展出,已无法看到铜镜正面。

图3-1 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唐代螺钿高士宴乐镜(霍宏伟摄影)

图3-2 国博藏唐代螺钿高士宴乐镜正面左侧(霍宏伟摄影)
古人将明亮清晰的铜镜称为“明镜”, 镜面模糊不清的称为“昏镜”,正如将破损模糊的纸钞称作“昏钞”一样。唐代刘禹锡有一首诗作《昏镜词》(《全唐诗》卷三五四):
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
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
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
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
饰带以纹绣,装匣以琼瑛。
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
有人说这首诗的意思是,人们很少直面自己的缺点,不用真正的“明镜”,却将那些善于遮丑的“昏镜”视为宝贝。另有人结合唐朝的历史背景提出,此诗含义深远,以“明镜”喻贤良,指唐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以“昏镜”喻奸邪,指宪宗宠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是指宪宗。
除了中国境内所见出土唐镜资料以外,在日本皇室的文物宝库正仓院,还收藏着一些珍贵的唐镜传世品。这些镜子从未埋葬于地下,一直被人视为珍宝,倍加珍惜,秘藏于宝库内。2004年,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举办的第五十六回正仓院展览中,展出一面来自北仓直径达43.1厘米的大型双鸾瑞兽镜。镜背伫立的双鸾、奔跑的瑞兽、浮动的祥云,禽兽纹饰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遗憾的是,镜面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虽无锈迹,却暗淡无光,甚至可能是由于长期放置于朱色木质镜盒内,导致镜面局部还粘上了一些暗红颜色。
正仓院南仓还珍藏有一面特种工艺镜,即鎏金银背山水八卦镜。镜背鎏金,錾刻山水、人物、动植物、八卦、铭文等各类纹饰,精美绝伦,令人惊奇,堪称一绝。与镜背纹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面氧化较为严重,不仅毫无光泽,而且还有一些带子捆绑的痕迹印在了镜面之上,看来如何有效地长期妥善保存铜镜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
宋人刻画
不论是汉晋铜镜,还是唐代镜子,都是日常生活中照容理妆的实用器具。谁曾料到,到了五代、北宋时期,镜子已不再仅仅是世俗社会普通的家庭日用品,而是进入佛国净土,担当起一个重要角色,佛教信众在镜面上以细线錾刻佛教题材的图画。
许仙与白娘子的千古传奇,让杭州雷峰塔闻名于世,妇孺皆知。2000-2002年,考古学者对雷峰塔塔基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清理,在地宫内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有一面五代时期的瑞兽铭文镜,正面以阴线刻有一幅画,画面构图完美,内容丰富,有学者认为这幅画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佛教中的西方净土。
1987年,在对浙江黄岩灵石寺塔进行整修的过程中,于该塔第四、五层放置的铁函内,发现北宋线刻铜镜6面,其中5面镜子正面分别线刻释迦牟尼及弟子像、四大天王像(图4-1、4-2)。这些镜子保存良好,制作精整,应该是佛教信徒专为供奉此塔而特制的铜镜。

图4-1 浙江黄岩灵石寺塔出土宋代北方毗沙门天王镜正面(《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

图4-2 浙江黄岩寺塔出土宋代北方毗沙门天王镜正面局部(《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
中国古人一直讲究阴阳平衡,凡事总有两面性,正如《易·系辞上传》所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镜子是个“两面派”,照镜子能从中读出辩证法,那需要一定境界。镜面,存储着多少容颜的历史记忆,如今却只能是忘纷华而甘淡泊;镜背,则由古时的配角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主角。背面繁缛复杂、形式多样的各类纹饰成为今人驻足、凝视良久的视觉中心。
古人用镜,主要是看正面照容;今人赏古镜,更多地是玩味背面的纹饰及制作工艺。从实用到艺术,从欣赏自我的美,到感受镜子的美,审美的主体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位移。在欣赏了大量古代铜镜背面纹饰之后,越发激起广大读者对古镜正面的好奇心,这篇小文或许能基本满足大家对镜面模样的期待。
每当我看到铜镜正面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想起古镜原来的主人,想象一下镜中古人的容颜,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似乎只能用唐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全唐诗》卷一一七)中的诗句来表达我的思绪: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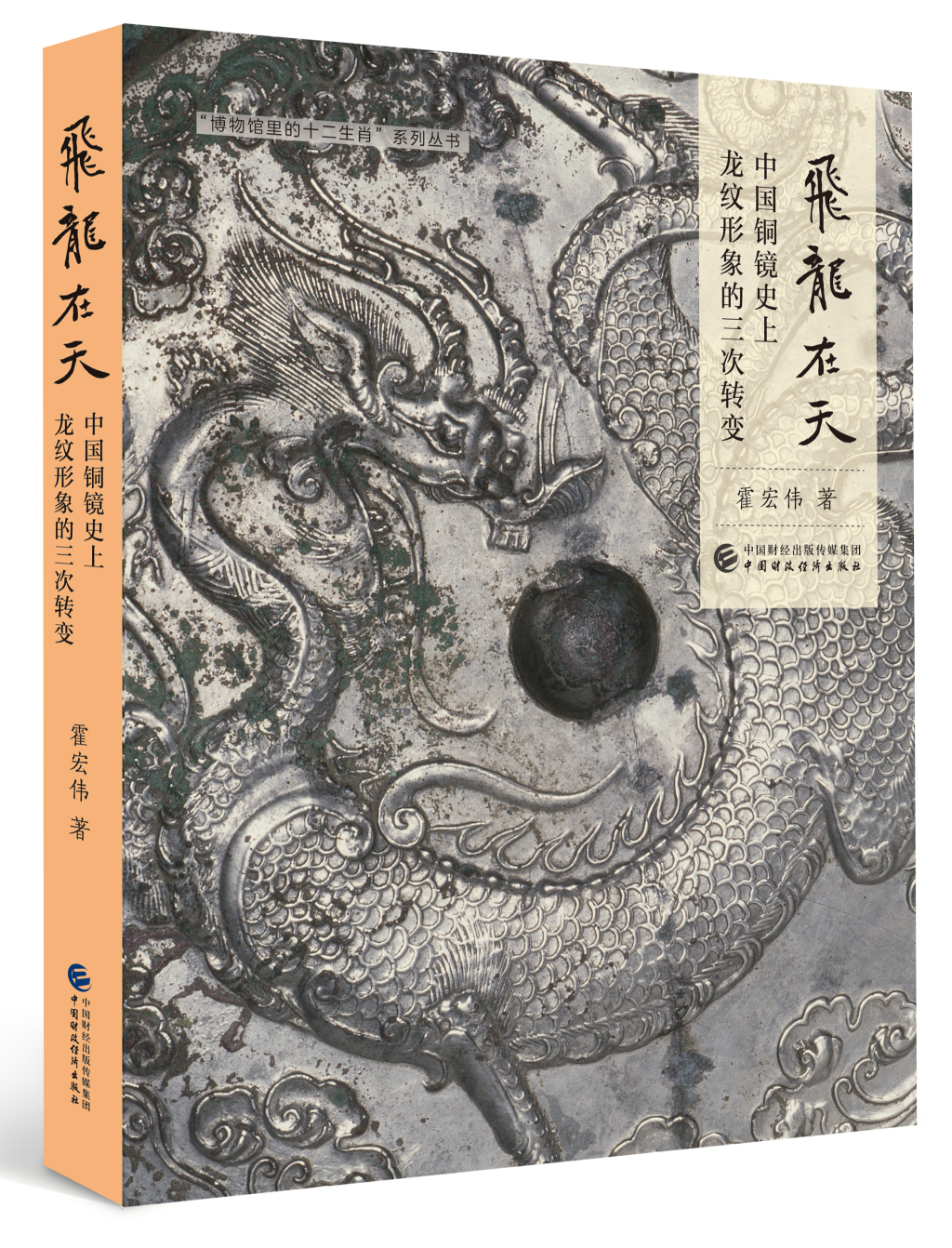
(本文摘自霍宏伟著《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5年1月。作者对原文做了修改,注释从略。)








 蜀ICP备2022028980号-1
蜀ICP备2022028980号-1